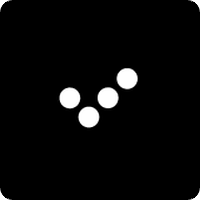中国市场经济之路
凤凰财经: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学习的是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当时他们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后来我们是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的?
吴敬琏:在改革派里面,研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代表性是孙冶方,东欧的代表人物是波兰经济学布鲁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是非常反对的,经济学家到了80年代后期,没有人再赞成市场社会主义了。
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它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保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使企业在运作的时候,要让市场起一定的作用。所以孙冶方总结市场社会主义时候说,就是“大权独揽”。
凤凰财经:市场社会主义和我们以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是不是一回事?
吴敬琏:不是一回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加了一个“帽”叫做“有计划的”。这个是赵紫阳为了从中共十二大过渡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概念,在中共十二大上规定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起辅助性作用。
赵紫阳采取了一个策略,先是用马洪写的一个论文,然后他放了试探气球以后觉得有可能通过。马洪的论文是1984年7月写的,赵紫阳是1984年的9月9号在中央文献里面有他给中央常委写的东西。
他说,现在看来我们对于计划经济应该这样理解:计划经济不等于都是指令性计划,应该是指导性计划为主,我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解应该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说实话,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把所有的定语都去掉,意思就是:计划经济就是商品经济。
凤凰财经:这没法划等号的。
吴敬琏:他这个话好像逻辑不通,但绕来绕去,后来好象还挺能让大多数人接受,并且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通过以后大家所记得的改革目标就是商品经济。这个意见在经济学家里面薛暮桥提出的,他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商品经济,不管做多少定义,多少个定语加在上面,落脚点就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就是让自由价格去决定资源配置,所以市场社会主义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不是一回事。所以90年代以后,就没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了,即使在东欧这种提法也没有了。东欧在剧变以后,他们根本不说是改革,匈牙利人根本不承认这叫改革,他们认为是恢复。我记得1988年*的一次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维也纳举行,匈牙利的经济学家在会上就说了个怪话,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
塑造道德秩序不能忽视市场的力量
凤凰财经: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真正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很多民众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结成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比如说高房价是市场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市场造成的、然后空气污染也是市场造成的。
吴敬琏:是的,这种事情已经说了10年了,这是过去10年出现的一种现象。最初从医疗改革说起来的,这是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始的,他们把看病难看病贵的归因于医疗的市场化。(编者注: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后的医疗改革造成医疗改革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底下,并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吴敬琏:还有更严重的,就是谴责医生,后来就变成了打医生、杀医生。
凤凰财经:实际上医生被妖魔化了。
吴敬琏:医疗实际上是制度上出了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报告,说是市场化出了问题,然后强调医疗是公益性的、是公共品,应该由公立医院来为全社会服务。但是又没那么多钱拨给医院,就叫医院创收,结果医院就乱开药了,以药养医,然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把这个问题说成道德问题了,最后造成现在这种状态,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凤凰财经:主要是现在我看医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好象停住了一样。
吴敬琏:是,因为国研中心定的基本方向走不动了,陕西神木就是一个例子。
凤凰财经:但是在在社会保障问题上,民众希望政府大包大揽,比如呼唤免费医疗等,但是政府是不创造价值的,还是要有纳税人来承担这些费用,尤其是中国这个长期以来民众怀念计划经济下的“父爱主义”怎么去引导公众,这个我们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吴敬琏:那当然了,而且上一任政府基本上顺应这种形势,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行不通的,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完全陷入困境,他也是搞民粹主义。包括俄罗斯的免费医疗,英国的医疗也有这样。
凤凰财经:还有阿根廷现在民粹主义路线也走不通了,好象南美很多国家都面临这种问题。
吴敬琏:关于阿根廷的问题,2003、2004年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争论,社科院方面研究批判新自由主义,说拉美经济危机有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也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这个时候,中财办也做了一个调查,他们也做了专门的调查,刘鹤写了一篇文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刘鹤的结论主要是说,民粹主义和军政府来回的碾压下,(拉美经济出现经济危机。)民粹搞不下去的时候,军政府发动政变就上来了,随后军政府实行专制,专制制度下民粹又上来了。这样就来回地弄,拉美经济积重难返。
但是现在在国内流行的都是社科院的结论。舆论上全部是批新自由主义的。
凤凰财经:三月份的时候,楼继伟在国务院发展论坛上说,要警示了民粹主义,“要帮穷人,不能养懒人。”
吴敬琏:楼继伟的这些话我看是完全说得对的。我们要帮穷人,不能养懒人。结果给骂得一塌糊涂。作为财政部长他是深有体会的,财政部如果继续这么大包大揽,他没法搞下去的。
民众往往都是这样,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福利,全世界都这样的。你看欧洲债务危机,德国人为什么不愿意救助希腊那些国家。因为德国人比他们勤劳辛苦,但是福利比希腊还低,然后当德国要求希腊减少财政赤字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些民众开始示威了。
凤凰财经: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希腊工人上班的时候不来,罢工的时候全来了。
吴敬琏:是,就是全世界都这种倾向,政府要引导,你不能去火上浇油,四处给民众许诺。造成大家对高福利抱有不切实际的心理,当许诺实现不了的时候,就用道德来指责医生、企业,然后也造成了仇富啊。
凤凰财经:您认为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不可以起到道德规范的这种作用,比如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使得自利的人必须为满足社会需求才能获利?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空气污染问题,是通过政府干预企业去解决问题,还是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更合理呢?
吴敬琏:市场不能完全起到规范道德秩序的作用,但是提高效率要靠市场。
提高效率是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基础,而要提高效率首先是要由市场去解决的。没有市场就不能提高效率,所以一定会造成污染越来越严重。
但是对于市场上的人的行为,市场不能够保证能够给他道德约束,所以要两手抓。贯穿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一生的就两本书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国富论》是说,面对着有私心的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一定要用市场使得他个人牟利的行为,符合社会的利益,不致于发生冲突。因为他一定要服从社会的利益,否则的话他的东西卖不掉的。那至于说他会不会造假呢?你就需要由政府去管了。还有一个就是内心的力量,这就提高道德的情操。
有一些人说,《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早期写,国富论是后期写,这话不对。他确实是先写的道德情操论,但是最后修订的也是道德情操论的课,所以他是一直坚持这样的两手。面对的就是有二重性的人,既有利己心,又有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建立一个市场制度,就是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让利己的人要服从社会的领导,但是还要增强他自我的约束力,否则的话,他老是想办法搞歪门邪道,那么就需要用政治的力量去管。
凤凰财经:就是要有法律和监管的规则,还要有他自己的约束,才能提高他的道德情操。
吴敬琏:所以现在出了这么多问题,然后指责企业没有道德血液,这是不对的,忽视了市场的力量。
不反思重庆事件难重塑企业家信心
凤凰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国企改革论述比较多,并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形式,您怎么看混合所有制在国企改革中未来起到的作用,在我们和一些民营企业交流的时候,部分民营企业家表示如果他们不控股的话,可能不愿意与国企成立混合所有制?
吴敬琏:这种里面并没有说谁控股。但是混合所有制不是新东西。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除了极少数要有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行股权多元化”。股权多元化就是混合所有制。
凤凰财经:那这次为什么又重新又提出了这个事呢?
吴敬琏:这是因为没有贯彻嘛。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很多事情后来都停了,而且往回走了。特别是这些年的“国进民退”,加上政治上的重庆事件对法治的破坏,企业家不敢跟政府和国企合作,现在看起来挺麻烦的。
凤凰财经:所以大家普遍地担心,虽然又把混合所有制重新提是不错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法治完善作为配套设施,民营企业家还是不放心。
吴敬琏: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了独立审判,但是不愿意触及和反思重庆事件的问题,没有明确地把这件事理清楚,反思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处理的方式就是错了就错了,偷偷的改掉,但偷偷地改革是不行的。一些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的心理没有变,他们认为这是薄熙来做的是好事,如果不把这个心理扭转过来,就没有办法消除企业家恐惧。民营企业家敢来吗?所以这是一种困境。
要把“田面权”还给农民
凤凰财经:土地是朝正确方向走了,但是说得有一点模糊。所以在解释权上大家争论起来了。而且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保障,农民把土地卖了以后,到了城市找不到工作成了流民怎么办?
吴敬琏:这是老观念了,2002年中央要换届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主要召开了一系列了座谈会。其中一次座谈会就讨论农村问题的,这次会议开了两个半天,*个半天我有一个发言,我就讲到要把土地的田面权还给农民,也就是土地用益权。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们江浙一带,把土地所有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做田底权,一个叫做田面权。田底权就是狭义的所有权,田面权就是使用权。我就建议要把田面权还给农民,农民可以自由处置,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租赁、也可以买卖和流转。田面权在经济学上说就是取得这个级差地租的权利。
所谓级差地租就是这个投资所取得的超额收入,如果这个所有权不明晰,*的影响就是所有人不愿意投资。
我最近去了常州,就看到山区经济非常地好。为什么呢?因为山林产权是明晰的,是可以流转的。就凭这一条,那里的经济就弄得很好。土地可以流转,可以变成大农庄,而且农民愿意投资。比如一个地方是搞竹子加工的,就弄起来了。
我讲完以后,当时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似乎他们能够接受。
但是后半天的会议,轮到中央农村领导小组的同志开始讲,他们就说了土地使用权返还给农民的危害,后来中央领导比较认可他们的观点。所以后来修改的土地承包法就规定,土地只能流转的是承包权,也就是在承包期间的承包权,就这么下来的。后来主要反驳他们观点的是秦晖,秦晖写了很大篇的文章来反驳。(编者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曾在《社会科学论坛》发表《农民地权六论》,表示“如今有人极力强调土地是‘最后保障’,对农民非常重要,并以此作为土地不能归农民的理由”,“是一种颠倒权利义务的怪论,它把‘国家责任不能推给个人’颠倒为‘国家可以剥夺个人权利’,实在是很荒谬的。”)
所以土地问题从2002年一直到现在,弄了10年了没有突破,未来土地改革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就看中央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了。
凤凰财经:如果土地产权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会不会对未来的城市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吴敬琏:城市化问题的根就在这儿。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造城运动,就是因为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差价大,各级政府就是靠这个来弄钱。现在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口城市化的速度高一倍以上。
城市化的作用就是靠人的积聚来提高效率的,结果是土地城市化了,它起不到城市化的作用。提高效率的作用没有,但是城市化的各种毛病它全有。这些毛病都是因为城市规模太大造成的,诸如交通拥堵、生态破坏、成本提高等。
现在地方的这个债务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债务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造城嘛。因为土地成本低,各个地方都在造城,能够扩大城市规模,就能够通过申报,能够得到财政支援。所以说我们城市化受土地产权不明晰这个危害是很严重的,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
强化改革权威性更要强化法治
凤凰财经:现在中央准备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继续加强改革的权威性,这也被一些人认为新一轮的改革是一种集权式的改革,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如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
吴敬琏:改革没有权威是不行的,就像俄罗斯那样,我认识他们的体改委主任,他对我说,他们制定了很多不同的计划,结果都是白说了,根本出不了克里姆林宫的门。
凤凰财经:执行不下去,没有权威。
吴敬琏:要打破旧的利益格局,没有权威真还不行。但是强化权威这件事,跟政治改革的目标又是不同的。把什么事都集中在党中央,跟小平同志政治改革的*关就有矛盾的,小平同志政治改革的*条就是党政分开。
改革措施要执行下去,确实需要很大的权威,强化权威又与政治改革目标相矛盾。我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强化法治的基础上树立权威的政府。
一定要强化法治。政治改革当然还包含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民主选举等,但是当前民主选举这个目标太高了,法治一定要同时加强,否则的话要出事。